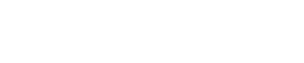《外交》季刊
美國與伊朗的敵對及其對國際地緣政治的影響
華黎明 中國前駐伊朗、阿聯酋、荷蘭大使
美國與伊朗的關系是當今世界上最敵對的雙邊關系之一。雙方斷交達四十年之久。前者視后者為“邪惡軸心”,對后者使用了除戰爭以外的一切孤立、制裁、顛覆、軍事包圍的敵對手段;后者視前者為“大魔鬼”,竭其所能擴展自己勢力,企圖將前者趕出中東。美伊將近半個世紀的敵對是20世紀美蘇冷戰的衍生物,導致了大國關系的多層博弈、中東各種勢力的重組、國際油價的波動乃至美國全球戰略的部署。2015年伊朗核協議簽訂后,美伊關系曾有過短暫的緩和。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宮后,美伊關系再度劍拔弩張,正在走向危險的邊緣。
美伊關系敵對的根源
二戰結束,冷戰開啟,伊朗就成為美國在全球戰略布局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棋子,北可遏制蘇聯南下,東可俯視南亞次大陸,西可進軍阿拉伯世界,南可控制波斯灣、印度洋的戰略和石油通道。1953年美國擔心蘇聯勢力南下滲透,中情局策劃政變推翻伊朗民族主義的摩薩臺政府,扶植親美的巴列維國王統治,在伊朗埋下仇恨的種子。1955年美國又拼湊由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組成的《巴格達條約》組織(1958年伊拉克退出后改名為《中央條約組織》)。美國控制伊朗達1/4世紀。1979年,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推翻了親美的巴列維政權,占領美國大使館,扣押美國外交官,宣稱輸出伊斯蘭革命。1980年卡特政府宣布與伊朗斷交,美伊敵對從此走上不歸路。1980年兩伊戰爭爆發,美國支持伊拉克和沙特等阿拉伯國家打擊伊朗。八年戰爭,伊拉克得到源源不斷的支持,而伊朗則孤立無援、損失慘重,耗盡了國力。1988年,美國文森斯號軍艦擊落一架伊朗民航客機,269名伊朗人罹難,激起伊朗全國公憤。伊朗反美從此成為全民共識。
“9?11”事件和美國發動的兩場戰爭徹底改變了美伊博弈的格局。伊朗乘機崛起,控制了伊拉克和敘利亞,影響力深入到阿拉伯心臟地帶,核能力迅速發展,美國在中東則顯得越來越力不從心。延時八年的敘利亞戰爭起源于美國和伊朗對敘利亞的爭奪。
美伊敵對40年的歷史表明,美國要維持世界霸權,不能容忍一個反美政權統治伊朗這樣一個戰略地位至關重要的國家,更不能容忍伊朗擁有核武器,擴展在中東的勢力范圍。改變伊朗伊斯蘭政權或迫其就范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和精英集團的共識和既定政策。任何人入主白宮都不會放棄這個政策,特朗普無非是其中的激進者。反美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立國之本,伊朗的執政者只能在與美國對抗的程度上做調整,在根本立場上別無選擇。
美伊圍繞核問題的博弈
伊朗核問題的核心是伊朗與美國的關系。1979年以后的伊朗是美國眼中的“問題國家”,所以它的“核”就成了問題。伊朗核問題的癥結一目了然。
伊朗的核技術研究始于上個世紀50年代,是在美國的支持和扶植下發展起來的,當時伊朗是美國的盟友。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伊朗由親美轉變為反美。40年來,美國歷屆政府無一例外都謀求推翻或改變伊朗伊斯蘭政權。9?11事件和伊拉克、阿富汗戰爭發生后,美國眼看伊朗勢力坐大,挑戰美國在中東的戰略利益。對美國來說,核問題只是一個切入點,目標是以壓促變,矛頭直指伊朗現政權。
伊朗的經濟并不寬裕,仍要耗費巨資發展核技術,一是為確保自身安全,二是為了謀求核大國地位,都與美國有關。在美國巨大的壓力面前,伊朗表現得桀驁不馴。這是伊朗的求生之道。
兩伊戰爭和第一次海灣戰爭結束后,伊朗恢復了核技術的研發。伊朗的“核”成為全世界關注的“問題”是2003年以后的事情。
2003年,伊朗秘密研制核武器的計劃暴露,美國開始向伊朗施加強大政治壓力。美國主導和控制了這個議題的全過程。2003年9月,美國以伊朗違反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為由,要求將伊朗核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討論,對伊朗實施制裁。
防止核擴散是一個神圣的議題,是全球的責任,但是,美國卻將壓垮伊朗現政權的目標巧妙地包裝在核擴散議題之中,將整個國際社會拖入與伊朗為敵的漩渦。
2006年1月16日,在美國倡議下,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和德國代表在倫敦聚會討論伊朗核問題,啟動了專門討論制裁伊朗的(P5+1)六國機制。
2006年7月,美國通過P5+1機制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限伊朗在一個月內停止鈾濃縮活動的決議案,獲得通過。
通過同樣的路徑,美國分別在2006年12月、2007年3月、2008年3月和2010年推動安理會通過四個制裁伊朗的決議。
這個過程清楚地表明,美國在防擴散這面神圣的旗幟下將伊朗打成了世界的“公敵 ”,裹挾“5+1”機制和聯合國孤立和打壓伊朗。
以2013年魯哈尼當選伊朗總統為契機,美國與伊朗關系出現了戲劇性變化。美國總統奧巴馬想當非戰總統,并且要留下一份外交遺產,出現了美國對伊朗核問題立場的轉圜。奧巴馬為此嘔心瀝血,還不惜得罪盟國以色列和沙特。奧巴馬在當年聯大發言時破天荒地宣布,美國“不謀求改變伊朗政權,并尊重伊朗人民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赴紐約出席聯大的伊朗總統魯哈尼也向美國做出了改善關系的姿態。魯哈尼與奧巴馬通了電話,美國與伊朗從對抗走向真正意義的談判。奧巴馬與魯哈尼借助P5+1的平臺就核問題進行了為時21個月的認真的討價還價和艱苦的談判。伊朗以限制核計劃換取了美國和國際社會取消對其制裁。2015年7月14日P5+1與伊朗在維也納達成了解決伊核問題的最終協議--《全面聯合行動計劃》。聯合國安理會在一周后通過2231號決議確認了該協議。2016年1月1日,美國和國際社會取消了對伊朗的制裁。
特朗普與美伊關系的逆轉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后全盤否定了他的前任奧巴馬的伊朗政策,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敵視伊朗的總統。2018年5月8日,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國退出伊核協議。
從今年8月7日起,美國已重啟對伊朗購買或收購美元、黃金或貴金屬貿易、對伊朗進行的銷售、供應或進出口金屬貿易的制裁,對與購買或者出售伊朗里亞爾有關的重大交易、或在伊朗境外持有以伊朗里亞爾計價的大量資金或者賬戶的制裁,對購買、認購或者促成伊朗發行國債的制裁,以及對伊朗的汽車行業的制裁。按照特朗普宣布的計劃,從2018年11月4日起,美國政府將重啟對伊朗能源和金融領域的制裁,徹底禁止伊朗的石油出口,切斷伊朗的財源。
2016年美國政治大翻盤,傳統的政治精英被趕出政治舞臺,附和民粹聲音的特朗普在選民的簇擁下入主白宮,自然要否定前任的一切,并一一落實。伊朗核協議是特朗普要推倒的重要選項。
在美國,伊朗是個被深度妖魔化的國家,輿論普遍“仇伊”和“厭伊”。奧巴馬當年與伊朗談判和簽訂核協議在美國民意基礎薄弱。特朗普競選中和執政后推翻協議不費吹灰之力,稱之為“最糟糕的協議”。雖然退出協議有悖美國的國際信譽,在美國國內卻是提升票倉和民意支持度的利器。在民主黨和媒體揪住 “通俄門”事件緊追不放,拿伊朗核協議說事,可以為特朗普贏得更多的鮮花和掌聲,確保共和黨中期選舉不輸。
伊朗擁有核能力打破了以色列在中東的核壟斷,以色列絕不容忍,必欲除之而后快。要達此目的,以色列只有拖住美國才能如愿。奧巴馬與伊朗核談判,簽訂核協議導致美以關系惡化。特朗普上臺后立即反其道而行之,對伊朗示惡同時向以色列頻頻示好,當選后一百天首訪以色列,不久又宣布美國將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
盡管特朗普的制裁氣勢洶洶,但是還會受如下因素的制約:1)美國盟友和其他國家可能將不予配合,其中中國與美國發生了貿易戰,配合美國制裁伊朗的可能性不大;美國難以說服歐盟再次對伊朗制裁,而且歐盟將利用1996年曾經出臺的法律,對歐盟企業實施保護;俄羅斯、土耳其和印度也不愿意配合美國對伊朗再次制裁。2)與2012年的伊朗原油禁運時期相比,目前世界石油市場可以快速彌補伊朗石油供應減少的缺口。3)目前,美國政府還無法對伊朗的原油出口進行監督等,將使此次制裁效果大打折扣。
美伊敵對對國際地緣政治的影響
一、中東重組
冷戰期間,美蘇在全球爭奪勢力范圍,中東是雙方明爭暗斗最激烈的地區之一。阿拉伯人與以色列打了五次戰爭,主軸是巴以沖突,但背后都有美蘇的影子。冷戰年代,伊朗的巴列維政權充當著美國包圍蘇聯的前哨和與沙特一道為美國在中東和波斯灣看家護院的雙重角色。
1979年伊朗政權更迭,由親美轉向反美,美國的勢力范圍被迫從蘇聯與伊朗的邊界撤退至波斯灣南岸。這是冷戰后期,美國全球戰略遭受的最重大的打擊。
上個世紀80年代,伊朗的伊斯蘭政權在兩伊戰爭中被嚴重削弱。1991年蘇聯瓦解,第一次海灣戰爭爆發,伊朗在美國頻繁的制裁下苦撐。
冷戰結束后,美國獨享中東霸權十年。“9?11”終止了這種局面,兩場戰爭之后,伊朗獲得了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期,控制了戰后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西部,與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結盟,通過黎巴嫩真主黨直抵阿拉伯心臟地帶和以色列邊境。同時,研發核能力迅速提高,接近核門檻。
伊朗的崛起改變了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中東不再以巴以對抗而以美國和伊朗劃線,各種勢力重新洗牌、組合和站隊。伊朗成為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頭號敵人,巴以沖突被淡化、邊緣化,取而代之是,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為一方,沙特、阿聯酋和埃及為另一方的對峙。2011年在“阿拉伯之春”呼聲中爆發的敘利亞戰爭實際上是美國帶領一批中東國家試圖斬斷伊朗的戰略鏈條,2015年俄羅斯介入后加入了美俄博弈的因素,各方將敘利亞戰爭變成代理人的戰爭。此后發生的也門戰爭和沙特-卡塔爾斷交等事件都與伊朗有關。
當前伊朗-沙特的對立是中東國家親美和反美之爭,而決非美國媒體描繪的伊斯蘭教遜尼派和什葉派之爭,這是美國動員阿拉伯國家反對伊朗的蓄意的誤導。
二、美歐因伊核而對立
隨著柏林墻的倒塌,跨大西洋聯盟的基礎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歐盟已成為一個獨立的整體出現在國際舞臺上。歐洲雖然還是美國的盟友,但是不甘心再充當小伙計了。實際上,在冷戰結束后,除了反恐、防擴散和北約東擴,美歐的共同語言已經越來越少,歧見和摩擦卻越來越多。隨著特朗普入主白宮,美歐關系進入嚴冬。伊核問題是重要標志。
歐美在伊朗的利益不同,理念不同,面臨的問題也不同。歐洲對伊朗的石油供應和市場依賴很深。冷戰結束后,美歐對待國際關系的理念也逐漸分道揚鑣。歐洲各國內存在著龐大的、游離于乃至敵視主流社會的穆斯林社團,牽制著歐洲對伊斯蘭國家的政策。而美國政府的中東政策則歷來受制于猶太人集團。歐洲不認同美國推翻伊朗現政權的政策,更不愿失去擁有八千萬人口的伊朗市場。
2013年美伊關系松動,歐洲全力支持。在P5+1與伊朗長達21個月的談判中歐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2016年對伊朗的制裁解除后,歐洲的跨國公司和銀行蜂擁而至伊朗,獲得大批訂單與合同。而次年美國新當選的總統特朗普揚言要退出伊核協議,歐洲政客和高官紛紛赴美游說。2018年上半年法、德、英三國領導人分別訪問華盛頓試圖說服特朗普,均無功而返。5月8日,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后,歐盟對抗美國,8月份通過了阻撓法案,9月份通過“特別目的載體”的建議,使歐盟公司免于受到美國對伊朗制裁的影響,執行自己的伊朗政策。
美歐關系破天荒在一個重大國際問題上完全走到對立面。
三、中美關系因伊核而添新結
1979年伊斯蘭政權在伊朗執政后,美國和伊朗由盟友轉為敵人,而中國繼續保持并擴大了與伊朗的正常的友好關系,美國對此是有戒心和疑慮的。這個問題多年來始終是抑制中美關系的消極因素之一。
2003年伊朗核問題浮出水面。中美都主張維護國際防擴散體系和伊朗棄核。但是在涉及對伊朗進行制裁和動武等問題上,中美的意見又常常相左。
伊朗是西亞地區的大國,其戰略地位和豐富的能源對中國都十分重要。但是,在伊朗核問題上,美國是當事國,歐盟是居間調停的一方,俄
羅斯是深深卷入的一方。而中國則是相對超脫的一方。在伊朗核問題的舞臺上,中國不是主角,但又擁有關鍵的一票。
2010年后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伊朗第一大貿易伙伴,中伊貿易額達500億美元。中國從伊朗進口原油穩步增長,2017年為3150萬噸,占伊朗石油出口1/4,占中國進口石油7.4%,中國投資興建的鐵路、地鐵、電站、石化、汽車制造和水利工程項目遍布伊朗各地。
在中美關系40年的歷史中,美國要求中國的伊朗政策與美國保持一致,在伊核問題上擔心中國一票否決。伊朗在國際上孤立,在美國又被深度妖魔化,因此中伊關系的發展始終受美國制約。
最近,美國的對華政策發生重大轉折,美國精英集團對中國迅速趕超的焦慮和不滿都化為特朗普的對華政策,貿易戰、臺灣、南海和印太戰略一擁而上,延續了四十年的傳統中美關系遭遇嚴重挑戰。特朗普退出伊核協議,制裁伊朗,對于伊朗有貿易來往的各國將實施“長臂管轄”。中國是伊朗石油的最大買家,美國對中國企業揮舞制裁大棒不可避免。美政府對中興公司的處罰就因伊朗問題觸發,對中國企業和銀行是“殺雞儆猴”,中美關系必將平添一項伊朗問題。
然而,時隔十五年,伊核問題今非昔比。彼時美國以防止核擴散的名義動員國際社會圍剿伊朗,伊朗是孤立的。此時,特朗普退群,引起世界的公憤,美國是孤立的。
特朗普在退出伊核協議問題上一意孤行,強力推行制裁,引發美伊的全面對抗,后果嚴重。但是,經歷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的美國在中東已力不從心,再打第三次戰爭不可設想。這是制約特朗普在伊核問題上走向極端的重要因素。